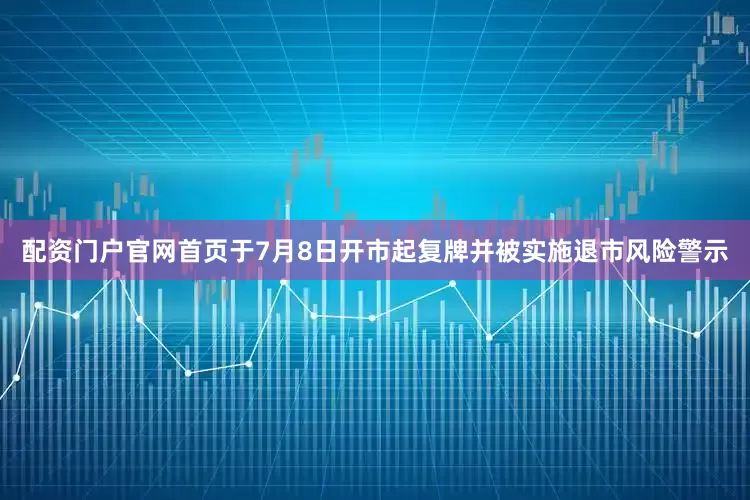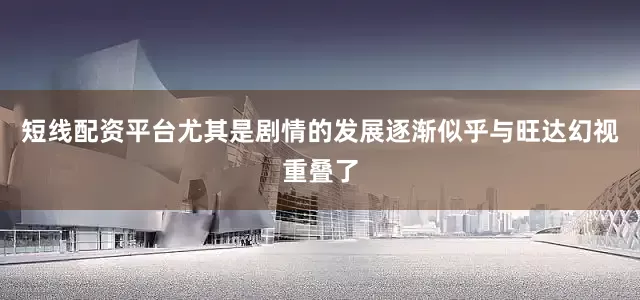人文学科、语文教育如何面对快速发展的AI时代,经典阅读在当下如何开展,什么样的语文教育能够守护下一代的成长和发展?9月5日,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、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、人民教育出版社、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、《南方文坛》杂志社联合主办的“‘文学生活’与‘语文教育’: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拓展的空间与路径”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,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共话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和语文教育事业发展。
语文教育能从“文学生活”引入什么
文学生活与语文教育的关系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。作为“文学生活”概念的首倡者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教育部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温儒敏谈及自己为什么提出“文学生活”的动因:“其中一个原因,就是对圈子化的文学批评、文学研究感到有一点闷,想打开一扇窗户,因为我们的研究评论包括文学史都是围绕作家、作品、批评家这个圈子进行的,但普通的读者当时怎么想呢?”
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烨看来,“文学生活”的提出将普通国民纳入了文学研究的视野,“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界都只关注精英作家和精英读者,而‘文学生活’的提出把普通受众和大众提高到了应有的地位”。
毫无疑问,这里的普通受众也包括广大教师和学生。“如果从学校教育的角度看,最广大的‘普通国民’正是数量巨大的中小学生。”湖北省荆州市教科院教研员余映潮提及自己从2000年到2025年这25年间的实地观察,在聆听了3000多位语文教师的现场课后,他得出一个令人忧心的观察结论:很少有语文教师关注学生的文学知识教育。有一定深度的文学知识教育,在教学中几乎不占比例。
展开剩余67%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余映潮认为,根源在于许多语文教师已经习惯以解析课文内容为主要的教学重点,以教师提问为主要方法带动学生的学习。而这种模式下,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往往缺少文学的知识含量,因此难以真正实现对学生文学素养的提高。
“在课堂阅读教学中,结合课文学习渗透文学知识的教育,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这种渗透能影响到学生以后的日常阅读习惯,影响他们长大之后的文学品位。”余映潮表示。
“语文教育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,关系到国民素质提高和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。”教育部教材局副局长刘宏杰表示,在当今时代快速发展的背景下,语文教育应坚持内容为王、应用为要、人才为本,更充分地体现中华文化的精髓,真正实现以文化人、培根铸魂。
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看来,应该将文学研究中的人文关怀、审美判断与现实感知能力引入语文教育,推动语文教学从“教文”转向“教人”,才能实现文学生活与语文研究的贯通和互补。
学生应该过什么样的“文学生活”
因为语文学科的基础性和关键性,近年来中小学语文教育一直备受关注。
“究竟我们的学生需要语文课为他们提供什么?我们的老师又应该如何引导?在此背景下,我们是否可以转换思路:不只是关注学生的‘语文学习’,而是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学生的‘文学生活’。”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尤炜认为,语文教育的研究方法应跳出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学或者课程论,进入到更丰富的交叉学科研究当中。
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编辑室主任徐轶看来,在实践层面亟须进一步强化文学对儿童的作用,让“文学生活”的观念在语文教育中扎根,在语文教学中成为一种自觉。
事实上,已经有学校进行了探索。研讨会上,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介绍说:“如何让孩子过上有深度的文学生活,我们的回答是‘师生共鸣’。为此我们设计了‘儿童眼中的鲁迅博物馆’项目,让孩子通过自己的视角和理解来认识和致敬这位文学巨匠。”
如何走出“兔子洞效应”
“IT文化现在如狂风暴雨覆盖了整个社会,有很多措手不及的新问题,我们来不及撑开雨伞就都成了落汤鸡,包括我们做文学研究的。”会议的最后,温儒敏在致辞环节表示,面对变化,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反思人文学科本身的问题。
这样的忧虑让很多人感同身受。
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韩卫娟坦言,手机等新技术正在重塑孩子的文学生活,并产生一系列副作用,要让孩子真正保持深度阅读的兴趣,实在是难上加难。
温儒敏特别提到,自己从一些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专家那边学到一个新词——兔子洞效应。“许多AI学习平台提供了大量游戏化、碎片化的信息和奖励,这样学习看似非常有趣,但是很难进行个性化的深度思考”。
“情感教育是基础教育的‘时代刚需’。但我们发现,很多学生情感表达呈现扁平化,共情能力也在发生变化。”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王本华看来,经典阅读恰恰能为情感沃土提供优质的养分,能帮助孩子校正方向,避免沉溺于碎片化阅读和短视频的狗血剧情。
面对这些问题,该怎么办?温儒敏引用了鲁迅的观点——“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,人生必大归于枯寂”。“一代有一代的学术,一代有一代的生活,我们要在变革中保持人文学科的品格和价值,积极回应时代的挑战。”
《中国教师报》2025年09月24日第1版
发布于:北京市我要配资网平台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168股票配资网距离 A β 假说提出至今已有 30 多年
- 下一篇:没有了